

叶雄记得22年前的那个晚上。在上海的一间办公室里,五名曾经的吸毒者刚刚结束在强戒所的戒毒宣讲,聚在一起聊天。
46岁的叶雄也是其中一员,出所还不满一年。她问大家:“你们觉得回归社会后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她设想了很多种答案:家庭不接纳、社会歧视、就业困难……
“没人和我们说话。”大家异口同声。这个回答出乎她的意料。
“我们有这个困惑,肯定很多人也有。”当天晚上,五个人讨论了杂志、报纸等多种媒介,最终决定以一条热线的方式,让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有话可讲”。这条热线被命名为“叶子戒毒热线”,取名自叶雄的女儿,是上海市建立的第一条戒毒热线。
 2009年,叶雄接听热线。 受访者供图
2009年,叶雄接听热线。 受访者供图
2005年,这条热线并入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更名为“自强戒毒咨询热线”。2014年,通过项目化运作升级成为坐标上海面向全国的公益性的24小时戒毒咨询热线。接线员从叶雄一人,发展到如今的21人团队,每天3人值班,力求做到全天候不间断。团队成员中不仅有禁毒社工、心理咨询师、律师、医生等,还有像叶雄一样,曾经历毒品危害,而后成功戒毒的“同伴志愿者”。
24小时戒毒咨询热线开通多年来,托举起了许多曾经误入歧途的求助者。同时,“同伴教育服务模式”也融入了热线服务与社工并行,让有吸毒经历的人彼此支持。不少人正是通过热线与同伴的帮助,彻底告别毒品,与过去决裂。
电话两端
电话常常在深夜响起。有时甚至是凌晨两三点。
傅忠已经可以做到立刻清醒,小心托住对面复杂的情绪。电话那头的求助者,可能正经历戒断的痛苦时刻,也可能正徘徊在想要复吸的边缘。而傅忠的职责,就是拽他们一把,不让他们再次坠入深渊。
2019年,傅忠加入上海市禁毒志愿者协会,同时也成为一名24小时戒毒咨询热线接线员。
早年,叶雄在电视、报纸上投放过戒毒热线的号码,甚至还将自己的私人手机号也一并公开发布。用叶雄的话来说,因为药物滥用人群有其特殊性,所以对她来说,接听热线不分上下班,她只想“多帮助一些人”。彼时,叶雄每天用于接听热线的时间长达12-18小时,求助量之大,从她的话费就可见一斑:曾经有一个月,她的话费高达500元。
直到热线升级后,接线员不再只有叶雄一人,增加了几位志愿者。通过4000-870-626平台的排班、并线接听,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求助者可以随时随地获得专业服务。团队每天安排三位接线员值班。有电话打入时,第一次序的接线员会首先接到电话,如果没有接听,则转接至下一个接线员,直到电话被接起。接听完毕后,接线员会将来电者的基本信息填入记录表,并将大致情况分享到群组,以便其他接线员接听到同一人来电时,能更全面地了解情况。
24小时里响起的来电,不只来自上海,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白天和夜晚的来电风格也不一样。接线员们发现:白天打来的电话,语气往往直截了当,有的是来求助,有的直接说事。
夜晚,往往是情绪波动更大的时候。很多情况是,来电者想要找人倾诉,却又没办法和周围的人吐露心声。傅忠发现,这些年,越来越多吸毒、戒毒者本人的电话往往会在这个时候拨进来。一旦接通,起码半个多小时。
也有家属替亲人求助。这类电话通常在白天家中无人时打来。“有的电话我们需要用固定电话回拨过去贝股通,而大多数家属却不会接。”上海禁毒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金伟静说。
最初,大多数来电家属会以“朋友”或“朋友的孩子”代称当事人。接线员不会多问,只在他们陈述需求后,尽量给予合适的回应。
信任,是在一次次交流中逐渐建立的。一位父亲在多次咨询后,才吐露实情:儿子不仅吸毒,还感染了艾滋病。医院、戒毒所都不便收治。他一次次把希望投向这条热线。后来,热线的帮助从线上延伸到线下,金伟静持续给戒断中的男孩写信、寄书鼓励。直到几年后,男孩彻底戒掉毒瘾,他们仍保持联系。
当然,在这里,接电话远不止简单的一问一答。傅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接线时的茫然。对方倾诉了四分多钟,当时几乎没有专业储备的他,不知该如何恰当回应。他有些懊悔,觉得自己几乎搞砸了。
后来,傅忠学习了一系列接听热线的话术,“即使我们没法在电话里迅速作出指导,也要想办法立刻转接到社工或者精卫中心。”在禁毒协会,每位接线员手上都有几页纸,印满了各类专业机构的联系方式。
时间久了,接线员们渐渐发现,自己能给求助者的,或许不仅是专业。更多时间,接线员要做的,是充当一个遥远的树洞,倾听、陪伴,托住电话那边摇摆不定的迷茫者。
这样的来电不是个例:有一次,一位戒毒者打来求助电话称,家里人已经放弃了自己,独自一人租住在外,夜深毒瘾上来后,他不知道找谁倾诉,只能选择拨打热线。金伟静说,“我们的理念就是陪伴。他打电话来的时候,也可以重新去吸毒,或许就不难受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说明他还是想戒,希望有人能陪着他忍过这样一个时间段。”那场凌晨的陪伴式聊天,足足持续了三个小时,接线员几乎一整晚都没睡。
接线员冰冰记得一次被误解的经历:那是一通她在外时突然接到的来电,当时周围嘈杂环境里的笑声传进电话那头,求助者立刻质问她:“你为什么笑我?”
“她以为我不尊重她、瞧不起她。”那是一位戒毒重返社会后,因吸毒经历被同事得知而遭到排挤的求助者。
这样的求助者,接线员遇到过很多。他们通常敏感、小心翼翼。很多次,为了让对方卸下防备,建立起信任,接线员会选择说出自己的秘密。
回归路上
当冰冰在电话里说出“我也曾和你一样”时,对方的称呼突然从“老师”变成了“姐姐”。
在热线中,像冰冰一样的部分接线员,经常需要完成这样的“自我暴露”。“表明身份后,忽然之间,关系好像就被拉近了。”冰冰发现,很多次,当她坦露自己也曾误入歧途,对面的语气会瞬间转变。
“同伴身份作为接线员,对求助者来说认可度会相对更高。”如今,在接线员里,有5位和冰冰一样曾经是吸毒者的志愿者。下定决心告别毒品后,他们也走过了一段重建社会关系、克服心理障碍的漫长之路。而现在,倾听热线那端的困惑,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
 接线员合影 受访者供图
接线员合影 受访者供图
傅忠在很多个电话里都“看见”过曾经的自己。有人向他倾诉想要复吸的挣扎,傅忠也想起自己刚刚戒断时的痛苦:浑身的骨头都像有蚂蚁在爬,难以描述的痒,让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强戒所里有人难受到极点,会忍不住拿起凳子往地上砸。
被送进强戒所前,傅忠曾一度背弃家人。父母把他反锁在房间要求戒毒,毒瘾发作时,他假意敲门,门一开就冲了出去,将母亲重重撞倒在地,头也不回。
接触到海洛因不到两年,傅忠就丢掉了在旅行社客户经理的工作,耗光几十万元的积蓄。17年里,傅忠每天起床都要拿起床头的毒品吸食,之后就去筹集毒资——向亲戚借,向朋友借,借完之后就到外面去借,“说难听一点就是骗”。直到他被送进强戒所贝股通,开始为期两年的强制戒毒。
有过相似经历的还有叶雄。入所前几年,叶雄尝试过无数种方法自我戒毒:服用120元一支的美沙酮口服液进行替代治疗,但药物太贵,身边尝试用此法的人也屡屡失败;找自愿戒毒康复机构,但叶雄戒断反应太大,会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拔掉输液针,又吵又闹,机构都不愿接收。叶雄记得自己被送入戒毒所的那天:“我和其他人一样,被一副手铐铐着送上警车,此刻的情景令我羞愧难当,难以忍受。”
然而,相比于生理脱毒,他们更难戒的,是心瘾。临近出所的一个月,傅忠彻夜难眠:出去,意味着又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毒品,他想起家里的抽屉里还有两包毒品,扔不扔?上家拿货的地方还留着电话,打不打?
很多从强戒所出来的人都经历过和他一样的纠结:如何面对家人?出去还能不能找到工作?对于他们来说,走出戒毒所,真正面对社会时,考验才刚刚开始。
“出去以后遇到了什么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自我的应对能力都非常重要。”傅忠感慨,如今在接热线时,他也会主动分享他的经历,“希望能够影响到对方”。
很多个电话里,戒毒康复者们都在反复讲述相似的苦恼:尽管已经戒毒很久,他们依然害怕被同事知道自己的过往,出门最怕在酒店、在火车上被警察抽查时周围人投来的目光。
有时候误解的态度甚至来自最亲近的家人。冰冰出所后,上班第一天被偷了手机,打电话告诉父亲后,却被怀疑是不是为了复吸耍花招。“毕竟自己犯过的错,要自己埋单。吸毒人员在社会的认可度肯定是相对较低的。”她觉得自己活该,但又一遍遍向父亲保证不会再犯错。
电话里也有很多抱怨:抱怨曾经吸毒的自己,抱怨来帮助自己的社工,甚至抱怨社会。傅忠非常理解这些情绪。他想起,自己刚刚出所时,路过邻居在小声说话,都会怀疑他们是在议论自己。耻辱感如影随形,久久不散。有次被禁毒社工邀请分享戒毒经历,他在台上看到台下观众交谈,“也许他们并不是在议论我,可我就是觉得他们看不起我。”
他向社工坦露自己的想法,得到了这样的安慰,“你对自己的认可,远比其他人要重要的多。”这句话,傅忠在心里记了很多年,如今,他也用同样的话在热线里鼓励其他人。
同伴
走出强戒所后,傅忠扔掉了以前的通讯录,和过去的自己做了一个了断。而他真正感觉到“新生”,是在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同伴巡讲后。
出所第四个月,社工邀请傅忠加入“海星同伴禁毒巡讲团”讲述自己的故事。第一次上台,社工对他说了句“请,老师。”傅忠感到震惊——还是戒毒人员的自己竟被对方称为“老师”。“有这样一份尊重,我是真的高兴。”
一段时间巡讲后,傅忠发现,自己的抱怨变少了。“那么多年,自己都处于一个自我封闭的状态,总是躲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现在当我走进阳光时,发现社会对我们这一类人,还是同情、鼓励的多。”
傅忠出所后的巡讲,正是上海“同伴教育”的一部分。2005年,叶雄的热线被越来越多受毒品困扰的人熟知。热线每次拨通,叶雄总是要聊一个多小时。即便她牺牲所有的空闲时间,帮助的人数也非常有限,而她也发现戒毒人员有在线下交流的需求。
此后两年,叶雄通过社工培训成为一名正式的社工,并自学心理咨询,她隐约记得,在她观看的心理咨询教学视频中,一位台湾老师分享了以团体为单位的心理咨询方式,她也想在戒毒领域做一个类似的小组。
2007年7月20日,经过9个月的筹备,叶雄将同伴教育的方法引入戒毒领域,成立了上海市第一个完全由有吸毒史的同伴组成的戒毒小组,旨在影响、鼓励、帮助在戒毒康复中的同伴保持操守、成功戒毒康复、恢复社会功能。
叶雄用“摇篮”来形容第一期的小组。她把自己出所后的经验和知识投入到小组的建设中,“摇篮”中的10位戒毒人员汲取精华,在角色扮演、当众演讲、同伴访谈等活动中逐渐减轻对毒品的依赖。由于涉毒人员以男性为主,而社工中多为女性,小组中的男性同伴会协助社工做尿检;同伴之间也会用活动中所学的内容,给所内的同伴写信,对社区康复的同伴做访谈。
第一期小组共十人,出所之后,只有一人复吸,与社会上流传的“100个人没一个能戒掉的”的观念相比,已是“不得了的成就”。正是因为同伴教育的有效,这种戒毒方法快速地普及开来。
2009年,金伟静第一次接触到同伴教育。当她把同伴教育带进戒毒所时,曾有民警质疑,“这些人每次都复吸,复吸又回炉,同伴教育真的有用吗?”
“有没有用,做了之后再看。”在金伟静的坚持下,强戒所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同伴教育,经历了多种戒毒方法的戒毒人员认为,同伴教育是最有效的一种。据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官网显示,目前参加同伴教育的戒毒康复人员操守率达80%。
“当他们看到与自己有相同经历的人也能去做这样一份工作,也能在社会中立足,就为吸毒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提供了可能和确定。”在金伟静看来,同伴教育的成功,能让家庭、社会一起来做这件事——戒毒绝对不是只靠一个人能坚持下来的事,需要很多的支持。
 接线员在接受培训。 受访者供图
接线员在接受培训。 受访者供图
这些年,同伴教育在不断发展,参与人数、活动频率都在提升,同伴教育的内容也在增加,有小组、沙龙、培训、同伴信箱、巡讲、同伴辅导、颁发涅槃重生奖、禁毒同伴志愿者星级评定等。在所内的同伴教育活动中,金伟静与其他同伴辅导员都会留下“24小时戒毒咨询热线”的号码,而这条热线的存在,也让迷茫的康复人员,找到一条方向。出所后,同伴教育依然在发挥它的作用。
热线的接线员们也在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一次,接线员接到一则来上海出差的海洛因成瘾者的来电,对方在酒店出现了严重戒断反应,打电话来寻求缓解方法。接线员没有过类似的经验,只能陪他聊聊天,让他喝点水,电话很快挂断。
后来,这个案例被搬到组会上重点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来电者处于严重戒断反应时,首先要了解来电者的具体位置和紧急联系人,保护来电者的生命安全,并且告知对方电话不会泄露隐私。同时,要尽可能保持通话,陪接听者撑过戒断反应最严重的时间。
那次讨论过后,团队又接到一则类似电话。第一天,来电者戒断反应严重,通话时长有5小时。她连续来电三个晚上,通话时长逐渐从5小时减到1小时,最终熬过生理上的戒断反应。后来,她一周来电一次,根据来电时间判断,她至少半年没有碰过毒品——对于自愿戒毒者来说,这已是非常罕见的坚持。
没有正常社交圈和社会支持,处于康复阶段的戒毒者很容易复吸。而这时,同伴们便成为他们重要的社会支持,组员们有共同经历、目标和语言。“人都是群居动物,需要朋友,同伴小组可以和毒友圈形成一种对抗,像拔河一样把戒毒人员拉回正轨。”部分同伴自愿成为同伴辅导员,从吸毒者转变为禁毒志愿者。
叶雄这样概括同伴教育的发展:“从一个人的独行跋涉,到一个团队的支持,政府和许多机构为同伴教育搭建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中,越来越多的生命因为同伴教育变得五彩缤纷。”
禁毒工作的不断完善,使吸毒人员数量大幅减少。据中国公安网数据,截至2024年底,中国现有吸毒人员74.7万名,同比下降16.7%;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人员428.6万名,同比上升5.1%。全上海以往容纳几千人的强制戒毒所,如今不到百人。
强戒所人数减少,但毒品类型在变化。叶雄发现,她所带领的同伴小组中,出现了滥用依托咪酯和右美沙芬的药物成瘾者,这给同伴教育带来新的挑战。
现有的同伴辅导员多曾吸食海洛因、冰毒等传统毒品与合成毒品,对于新精神活性物质了解较少,原先的防复吸经验不完全适用于现在的药物滥用者。为了消除隔阂,叶雄计划让同伴辅导员与药物滥用者本人及家属进行交流,了解戒断反应,改进沟通模式。面对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药物成瘾者,他们也会鼓励来电家属说服孩子亲自打电话,“他去说服孩子打电话的过程,就是一个他们相互沟通的过程。”金伟静说。
金伟静说,康复同伴禁毒志愿者的工作就像“拾星者”:
“沙滩上,小男孩和小女孩正在把被海浪冲到沙滩上的海星一颗颗捡起扔回大海,路过的人笑话他们在做无用功,因为下一个海浪过来,海星还是会被冲到沙滩上。小男孩小女孩笑笑说,能救活一个就是一个宝贵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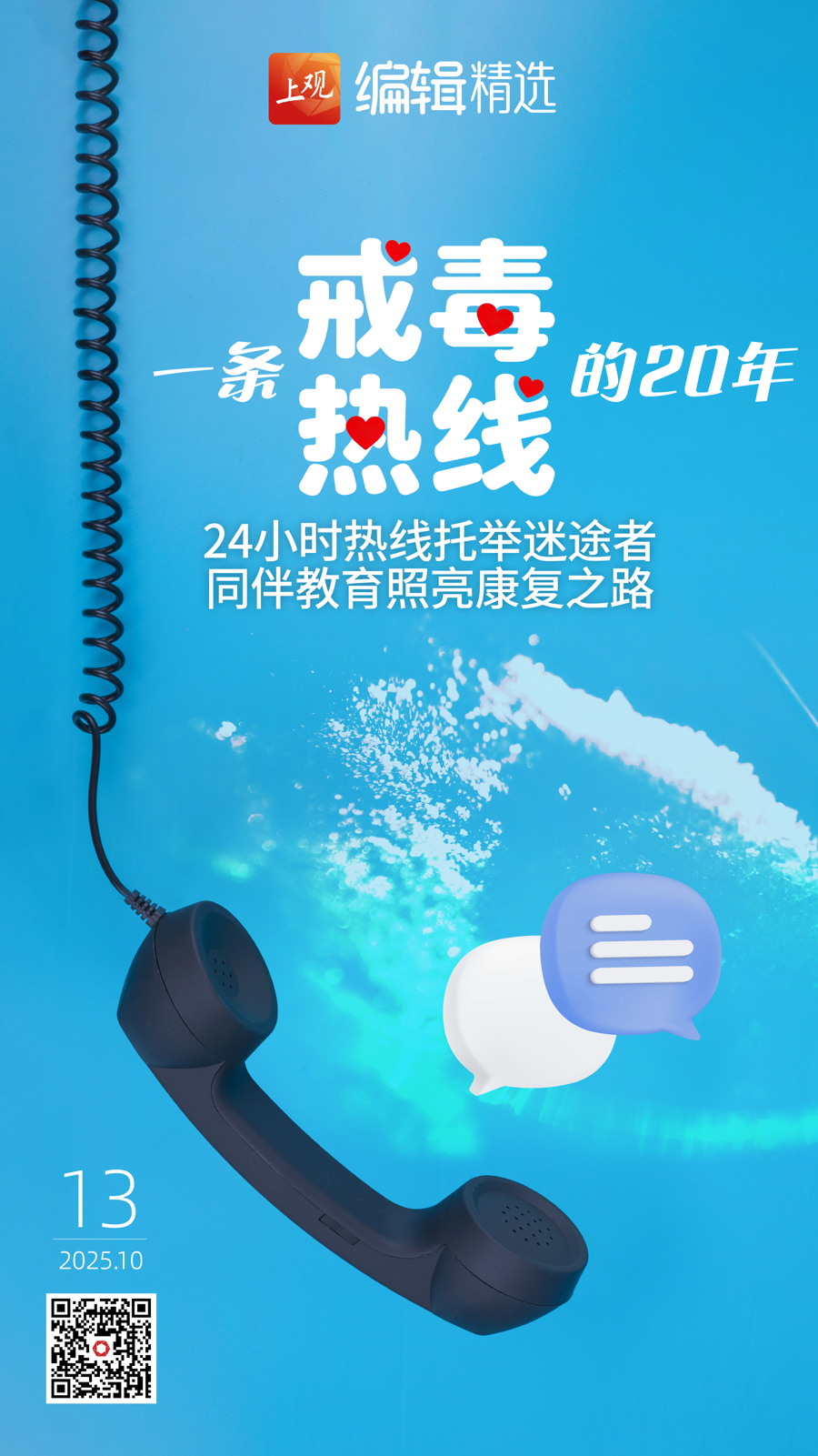 海报设计:曹立媛
海报设计:曹立媛
网眼查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